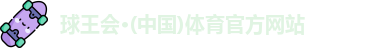20世纪美国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
国家行为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西方的研究一般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他和西德尼·维巴主编的《再论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1980)中比较详尽地历数了从柏拉图的《共和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对政治文化研究的贡献(Almond & Verba 1980:1-16)。不少学者也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看到了文化对于国家行为影响的观点,比如有的从中看到了政治文化的作用(Illés 2015)、现实主义理论(Monten 2006:3)和战略文化的相关论述(Zaman 2009:68),等等。
在美国,国家行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受学者关注。杰弗里·S. 兰蒂斯称,从社会科学角度开展国家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起形成数次高潮,历经四五十年代盛行的民族特征(national character)研究、60年代兴起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研究和70年代兴起的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研究等阶段(Lantis 2006:4-31)。本文参考兰蒂斯关于美国对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阶段划分思路,结合对不同阶段具体研究成果的分析,着重梳理和分析美国20世纪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历程及其特点。
二、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民族特征研究
美国民族特征研究的兴起,缘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信息需求。彼时的民族性格研究是基于人类学范式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鲁思·本尼迪克特和杰弗里·戈勒。前者的代表作是《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后者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民族性格研究》(The American People: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1948)。
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效力于美国战争信息局(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又译美国战争情报局),担任相当于处长的职务,发挥她的人类学专长,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本尼迪克特的本科专业是英语文学,一直到她转行人类学20多年后,还时常以不同的笔名发表诗歌。她在短诗《清除倒影的一汪水》中写道:“你是一汪水,被投下来的光泽清除了倒影,/水面像空气一样晶莹剔透,没有能耐/映出天上花瓣般的薄云,阵风吹皱——/绽开的美妙波纹,镶着太阳的金边。”从中不难看出,本尼迪克特细致的观察能力、情感的体察能力和现象的解读能力。应该说,她的文学素养给她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支撑。《菊与刀》的主要内容来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向战争信息局提交的研究报告,后经修改补充于1946年成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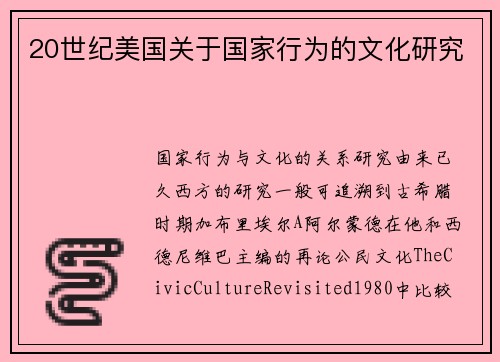
1944年,美国与日本激烈交战,本尼迪克特无法按正常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开展研究,尤其无法开展田野调查,故而她的研究主要参考包括日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献、剪报、电影、录音等资料。尽管如此,本尼迪克特撰写的研究报告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她提出的关于占领日本本土后保留日本天皇的建议被罗斯福总统采纳,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进展顺利(go smoothly)。《菊与刀》被称作应用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本尼迪克特撰写这份研究报告之时,美国和日本正处在惨烈的血与火的搏斗中,美军伤亡惨重,美国民众对日本无比愤慨。但本尼迪克特仍能以文学欣赏者的视角去研究日本文化,她用“she”或“her”来指代日本,从而保留了较多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战时研究容易出现的情感倾向。有评论者称,她客观地探索了日本魔鬼般表现(monstrosity)的动因。她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日本人在伦理道德上与西方人大有不同,日本人的道德观具有强烈的单选性,即将人生的义务分为“忠、孝、情义”等, 然后将这些德行“分别用包袱包起来, 分发到地图上不同的位置”(Benedict 1993: 195)。“日本人评论某人的德行如何,只就此人所应遵从的某一德行而论,如说此人是否‘忠’,或者说此人是否‘孝’,而极少综合评价。”(李霄垅 2008:107)应该恰是基于对日本价值观以偏概全特征的判断,本尼迪克特提出在美军占领日本后保留日本天皇的建议。日本人对天皇效忠的单选性,可以确保他们服从天皇的投降令。
球王会官网关于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评价态度,不少学者给予了肯定。例如,E. A. 胡恩伯尔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称,本尼迪克特的这一研究特点“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偏见,没有受政府态度的影响,甚至也没有受给她资助的战争信息局的要求的影响(Hoebel 1967:4)。同时,本尼迪克特对作为二战敌方的评价态度自然也遭到了部分美国学者的批评。有学者称,在保留日本天皇这一点上,本尼迪克特与日本右翼势力如出一辙,《菊与刀》的经典化为日本军国主义余孽提供了滋生的空间(Boles 2006:28)。
戈勒是英国人,但二战期间,他身在美国。戈勒与本尼迪克特有两个相似之处:其一,戈勒也为盟军做过民族性格调研,而且曾与本尼迪克特合作开展“远程社会人类学研究”。戈勒于1941年写成了咨询报告《日本性格结构和宣传》(“Japa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and Propaganda”),其自称报告“广为传阅,影响很大”。其二,戈勒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的第一学历专业是古典文学和现代语言,曾创作了一部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并写过几部剧本。然而,与本尼迪克特颇具文学欣赏性的超然态度有所不同,戈勒的民族性格研究颇受战时情绪影响(Hoebel 1967:4)。
戈勒民族性格研究的代表成果是《美国人民:民族性格研究》。在写作这部著作时,戈勒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涉及美国的40个州。他接触的阶层大致与他本人身份一致,因此调查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戈勒以美国阶层的流动性来说明他调查的阶层局限并没有影响他对美国民族性格研究的准确性(Kallen 1949:475)。在《美国人民:民族性格研究》中,戈勒从美国家庭、爱心与友谊、竞争与效仿等角度分析了美国的民族性格。戈勒的研究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但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融入美国民族性格的研究,且文风非常具有文学性(Kallen 1949:475)。
戈勒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来解释美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由于美国总体上是个移民国家,移民的后代有美国化的冲动,这就导致他们尽力摆脱父亲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反叛父亲的权威(被解释为美国反对权威民族性格的根源),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因此较低。移民的后代在孩提时代的恋母情结表现在通过自己的“成功”来争取和确保母亲的爱。这又培育了美国人的竞争性和效仿性。美国人将朋友多寡当作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此外,在与外人接触时,美国人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戈勒对此是这样解释的:美国人此时正经历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女性特质与其展现雄性角色的理想意识之间的抵牾(Singer 1949)。
美国的民族性格研究因二战信息需求而兴盛,却因其所基于人类学的研究视阈的局限而逐渐式微。M. 米德称人类学范式的民族性格研究是一种应急性研究,无不与国内士气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Mead 1953:642)。作为一种应急性研究,人类学范式的民族性格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期间和随后的50年代呈现出高潮。可是,“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人类学参与民族性格的研究从激情澎湃变成了仍有所延续的涓涓细流”(Hoebel 1967:2)。其原因主要是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与民族性格研究不甚吻合,前者更加青睐原始或土著部落的研究。人类学家对研究部落人的性格,甚至一个小镇人的性格尚有信心,但他们感觉民族性格这样庞杂的问题似乎超出了人类学研究的范畴。20世纪5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本尼迪克特去世之后,曾经从事民族性格研究的人类学家多有重操旧业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原始或土著部落等问题的研究。
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民族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与文学界的新批评有相似之处。前者从个人的性格形成和性格特征入手,寻找有差异的特质,努力分析出这些差异与研究者对该民族性格的总体印象的一致性。人类学范式的民族性格研究高潮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研究在民族身份、文化身份和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等研究中得以延续。其类似新批评的研究方法也像新批评的遗产一样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发挥着作用。
三、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的知识起源可以追溯到赫尔德、托克维尔、孟德斯鸠,甚至是古代世界的作者”(Formisano 2001:396)。但它的现代起源始于政治学,具体而言,是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文章《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在这篇文章里,阿尔蒙德提出了对民族性格等研究的质疑。阿尔蒙德认为“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等术语不是政治文化所固有的,这些术语“不稳定且意义重叠”(Formisano 2001:396),因此开始论述政治文化研究的可行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关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受到更多青睐。其间,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简称《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1963)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尔蒙德的教育背景是政治学。他进入芝加哥大学之时,恰逢其政治学专业大力倡导跨学科创新研究。阿尔蒙德称他很幸运,碰到了好老师和好同学。在二战期间,阿尔蒙德像本尼迪克特一样,也在战争信息局工作过。他负责研究敌方的宣传,而且担任了敌方信息(enemy information)处处长。《公民文化》的合作者。维巴本科时主修的是历史与文学,但是他对当外交官颇有兴趣,可能是这一兴趣最终使他成为政治学家。
《公民文化》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具有探索性,采用了当时比较前沿的调查统计方法,对所研究的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和美国)大约一千人进行了调查,而且关注了被调查对象的代表性。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文化分成三个层面:一是认知层面,二是评价层面,三是表达或感情层面。认知层面主要包括对事实发展或因果关系的基本认知理念;评价层面包括价值观、常规和道德判断;表达或感情层面包括情感附加、身份和效忠模式、认同/厌恶/漠然等态度等(Duffield 1999:23)。他们在设计的问题中询问了被调查对象对地方或国家的某条不公正法规的反应,获得被调查对象在认知、评价和表达方面的第一手数据。他们用格特曼量表对这些数据进行研究,从而分析被调查对象的“政治能力”(political competence)。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了五个国家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
该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政治文化角色。政治文化角色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公民型(参与型),二是顺从型(服从型),三是近视型(只关注身边、不关心政治型)。阿尔蒙德和维巴研究的结论是美国公民型角色占比最高,英国第二,德国第三,意大利和墨西哥最低。公民型角色占比高的国家会使国家精英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会影响他们的正常发挥;顺从型角色和近视型角色占比高的国家无法形成足够的压力使国家对形势变化采取及时有效的反应。从理论上来说,这三种类型的不同配比是一国政治文化的区别特征。
1980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又主编出版了《再论公民文化》。阿尔蒙德写了第一章,讨论公民文化的研究史。维巴写了后记,谈了《再论公民文化》的意义。这本文集收录的其他文章分别谈及公民文化或政治文化的理论视角和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这部著作之所谈基本是对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的评价。时隔近20年,回评《公民文化》观点的准确度,研究五国政治文化的延续和变化,讨论政治文化研究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还是颇有意义的。
从表面上看,《再论公民文化》书名强调的是“公民文化”,但这里的“公民文化”实际上指的是1963年的《公民文化》书名。《再论公民文化》着重讨论的是政治文化,与之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是书中所收录每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阿尔蒙德所写的第一章,主要篇幅都是在梳理政治文化自古希腊时期到出书时的研究历程。维巴在后记中则用“政治态度”“政治信念”等概念详尽地讨论了政治文化问题。关于五国研究的五篇文章的标题均有“某国的政治文化”的字眼。
美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仍可谓方兴未艾,“政治文化成了一个受欢迎的、被过度使用的时髦术语”(Formisano 2001: 393)。乔尔·H. 西尔贝认为,“我们好像生活在政治文化是解释和描述主导议题的时代”(qtd. in Formisano 2001:393)。20世纪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重心与语言研究的重叠性增强。例如,A. 斯威德勒将“文化”界定为“意义的象征载体,既包括信仰、仪式操演、艺术形式和纪念形式,也包括非正式文化实践,如语言、闲言、故事和日常生活仪式等”(Swidler 1986:273)。不过,由于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似乎都是很熟悉的术语,所以人们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追问不足,结果形成了这一术语形形色色的个性化理解,使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如同“把果冻钉到墙上”一样困难(Formisano 2001:394)。尽管对于政治文化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声音,同时由于所谓“行为革命”的出现,政治文化研究逐渐不再受美国政治学界青睐,但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仍在发挥作用(Lantis 2006:5-6)。
四、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战略文化研究
美国的战略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战略文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杰克·斯纳德的一份研究报告《苏联战略文化:对于有限核战争的意义》(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1977)里。在这份报告里,斯纳德列出了美国战略分析家的困境:他们怀疑以自己“正常的理性人”(generic rational man)思维模式去推测苏联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战略的可信性,他们对苏联相关文件的研读结果也不自信,等等(Snyder 1977:4-8)。斯纳德认为,跳出诸如此类困境的一个途径是研究苏联战略文化,因为“有理由相信,既然苏联战略文化遇到的是特有的问题,且是在特有环境中演化而来的,那么苏联战略文化一定包含某些方面特有的概念”(Snyder 1977: 9),而苏联的决策者不可能摆脱这些概念的影响。“既存的战略观念会对新技术的运用在纲领和组织上产生强烈的影响”(Snyder 1977:9)。斯纳德将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战略群体成员就核战略问题所共有的思想、有条件的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方式的总和”(Snyder 1977:8)。
斯纳德对于战略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强调引起了学术界和战略分析界的共鸣,战略文化研究得以广泛开展。在1995年出版的书里,约翰斯顿(中文名“江忆恩”)称,美国的战略文化研究已经历了“三代”(Johnston 1995:4-22)。20世纪70年代之后,战略文化研究在美国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且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不妨以约翰斯顿的代际划分为线索,考察一下美国战略文化研究的大概历程。
约翰斯顿将斯纳德当作战略研究的先驱,但未将其作为美国战略文化研究的第一代进行评论。他将柯林·S. 格雷看作第一代研究者的代表。格雷在他的《战略中的民族风格:美国的例子》(“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1981)一文中引用了斯纳德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Gray 1981)。在对斯纳德的定义进行阐释时,他补充了一些内容:“战略文化指的是关于使用武力的思想和行动模式,这种模式由对民族历史经历的感受而来,由为民族利益采取负责行为的愿望而来。”战略文化“由公民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来”,它“提供一种辩论和决定战略取向的氛围”(Gray 1981:22)。像斯纳德一样,格雷的早期战略文化研究重点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与否的战略选择问题上。约翰斯顿在划分战略文化研究的代际时,对格雷的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这使得格雷撰文(“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1999)来反驳约翰斯顿。在这篇文章中,格雷概括了战略文化第一代研究者的观点。
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源自雷蒙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认为文化由理想、文献和社会三个类别构成:理想是指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念;文献是指知识性或想象性的作品;社会是指文化描述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在制度体系和日常行为中得以表达(Gray 1999:52)。格雷对文化定义的溯源旨在说明第一代研究者对战略文化的基本观念:一是战略思想和行为模式均可称为文化;二是战略文化在独特的战略行为模式中得以表达(Gray 1999:54)。格雷对于战略文化既外在于战略行为又是战略行为(者)本身的强调,旨在区别于约翰斯顿将理念和行为进行分割的观点。总体而言,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者并不强调研究的学术性,而主要是针对冷战时期核战略的实用研究(Gray 1999:52)。因此,战略文化研究随着冷战结束、核大战威胁缓解而热度锐减。
约翰斯顿与兰蒂斯对于第二代战略文化研究的描述并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是约翰斯顿没有将自己列入第三代研究者的行列,他似乎将自己视为第四代研究者。而后来的研究者却认为他是第三代研究者的代表。鉴于此,我们采用兰蒂斯对第二代战略文化研究的描述,将以建构主义为特征的研究列为第二代(约翰斯顿倾向于将以建构主义为特征的研究列为第三代)。按照兰蒂斯的描述,第二代战略文化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阶段,战略文化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不再局限于核战略方面,而是延伸到了其他安全领域;二是研究重点转至战略文化和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上;三是战略文化中增加了许多新的概念形成要素,尤其是建构主义要素。亚历山大·文特是从建构主义视角研究战略文化的发起者。在《无政府状态是不同国家塑造的结果:实力政治的社会建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1992)一文中,文特称,他致力于用建构主义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Wendt 1992:394)。他认为,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是“有智慧的实践的社会建构”(Wendt 1992:392)。在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者看来,战略文化变化缓慢。一种战略文化尽管不是永恒不变的,但却会长期存在,它形成于某一群体形成的阶段,往往在其形成的时代过去之后依然存在,而且在这个群体经历的关键节口会发生逐步的或根本的变化。按照格雷的说法,要想在不同的年代(十年)间找到战略文化有意义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Gray 1981)。但在建构主义视角的研究中,战略文化被认为具有动态性,往往是建立在上一次战略选择及其后果的基础上,亦即因上次的战略选择而发展变化。
按照兰蒂斯的描述,第三代战略文化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斯顿(Lantis 2006:10)。约翰斯顿认为,战略文化是“一个综合完整的符号系统(如论证、结构、语言、类比、隐喻等),这个系统的作用就是确立普遍而又持久的战略选择取向。其确立的途径是解释人们对军事实力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角色和作用的观念,并为这些观念披上真实性外衣,以使人感觉这些战略选择取向具有唯一的现实性和有效性”(Johnston 1995: 46)。约翰斯顿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1995)被称作“战略文化研究的精华之作”(Lantis 2006:10),颇受同行称道。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美国战略文化三代研究历程的划分,而且由于质疑格雷等的研究成果而引发了战略文化研究界的论战。但是约翰斯顿将研究视点放在中国古代的兵书上,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具有当下意义,表明他认同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者的观点,承认一国的战略文化如果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变化缓慢的。同时他的观点也带有建构主义色彩。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战略文化:一种是象征性或理想化的观念,这些观念影响对不同战略选择的喜好;另外一种是操作层面的战略文化,其对战略实际选择影响巨大。操作层面的战略文化具有现实政治色彩,相对于观念层面的战略文化而言,有其建构性(Johnston 1995: X)。在评论其他第三代战略文化研究者对“常规”的研究时,兰蒂斯称第三代研究者立于文化主义(第一代)和建构主义(第二代)的交汇点上(Lantis 2006:12)。此评价对于约翰斯顿似也适合。
21世纪初,战略文化研究在美国达到一个巅峰,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专题学术会议比较频繁。但是进入21世纪十年之后,大部头的研究成果鲜见,对于战略文化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质疑声音有所增强。后现代的碎片化理念导致研究者对整体性研究产生怀疑,战略文化基金会(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网站依然发文频繁,但更多的是对具体事件的研究分析。
五、结语
不难看出,美国20世纪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因战争或危机而兴盛,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期则有所降温。进入21世纪后,“9·11”恐怖袭击又激起了美国相关文化研究的热潮。这一规律似乎告诉我们:美国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带有浓厚的问题意识,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来看,美国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有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和后现代之后过渡的特征。这一点与美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同向性。
在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新成员,引起了外国语言文学界师生的极大关注,他们对如何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展开了热烈探讨(参见李建波、李霄垅2019:11)。开展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采用文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是最便利的。总结和分析美国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历程,无疑对我国从文化角度开展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来源: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